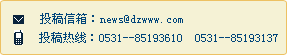■ 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从《国运1909》、《绝版恭亲王》、《辛亥:计划外革命》,到新作《天子脚下》,雪珥撰写的系列近代史书籍,为晚清改革始末打开切口,暴露出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。
□ 本报记者 卞文超
1月1日晚,雪珥从重庆飞抵北京。定居澳大利亚后,他频繁穿梭于国内国外,习惯于轻装简行。
雪珥发来的名片有两面。一面是“雪珥,非职业历史拾荒者、中国改革史窥探者”;另一面印着“蒋文胜,商人、律师、记者、朋友、澳大利亚太平绅士”等社会职务。随着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名声渐起,雪珥更多地以历史研究者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。读史而知兴替,其作品借古喻今的意味最为人称道。
1月份,他又有新作《天子脚下》面世。2日中午,在北京市朝阳区某酒店,雪珥穿着休闲装运动裤出现在大堂,言谈衣着都极随意,并不像想象中的海外“绅士”那样讲究。
行万里路
从体制内出走
从名字到身份,雪珥都难以让人一眼看透。虽然已有数本著作,读者对他本人却知之甚少,甚至不知他是男是女。
在和记者交流的三个多小时中,他十分健谈,表现出坦率的一面。雪珥原名蒋文胜,浙江人,干过公务员、记者、律师,后来下海经商,做房地产开发。1999年,他凭借50万字的财经专栏,技术移民澳大利亚。
有跨度、有纵深的生活经历,为他读史写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。
记者:采访之前看你的履历,感觉像一个谜。现在从事的主业是什么?
雪珥:目前国内国外两边跑,主业还是做生意、做贸易,读史写史是我的业余爱好。
记者:职业生涯发生了多次转变,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?
雪珥:我自认为是对社会现实接触比较早的人。17岁考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,在校就给校领导做助手,开始了解社会生活复杂的一面。1991年毕业后在浙江团省委工作,几年下来平均每年写25万字的文件,无形中锻炼了对改革风向的嗅觉。后来在报社挂职做管理工作,同时在多家媒体撰写财经专栏。
我感觉,读万卷书易,行万里路难。在机关跟着工作组到基层蹲点,让我受益很深。浙江大大小小许多县我都去过。这些经历让我看到了社会生活的真实,因此我不迷信文件,也不迷信教科书上的历史。
1999年6月30日,我踏上了澳洲的土地。到悉尼之后,在一家大型金融公司从事金融管理。2003年,回国下海,在上海做房地产项目开发。真正做生意我才知道,之前写的财经专栏完全是“站着说话不腰疼”。
地产项目的开发运作十分微妙和复杂,一个项目上有两百多个官司不足为奇。“非典”时期,我跑北京21次,和最高院的警卫都混熟了。我常说,房地产开发是“纸醉金迷密集型行业”,每天眼中都是大资本的运作,要去考虑各种关系的“勾兑”,也很容易让人迷失。
记者:忙于应酬哪有时间读史?
雪珥:看看我写了多少东西就知道,精力都放在那儿了。应酬除非迫不得已,因为不喜欢。尤其是到了澳大利亚之后,晚上商店很早就关门,街上黑灯瞎火的,几乎没有社交活动。每天晚上8点到12点,凭空多出4个小时的学习时间,可以真正静下心来写点东西。
记者:你解读历史的角度既不同于官方,也不同于学院派,这和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吧?
雪珥:正是因为我在一线干过,在潮头玩过,所以我不相信象牙塔里无菌环境下作的实验。我更倾向于把历史还原至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土壤中,思考实际问题如何解决。
细节比对
历史另外的可能性
从《国运1909》、《绝版恭亲王》、《辛亥:计划外革命》,到新作《天子脚下》,雪珥“在显微镜下看中国近代史”,为晚清改革始末打开切口,暴露出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。举个例子,他对保路运动的叙述让读者重新审视这段历史。
1910年,持续三年火爆的上海股市崩盘,川路公司股本形成巨额亏空,铁路建设没有进展。中央政府想将铁路收归国有,并拒绝为炒股损失的300万两白银埋单。川路公司借此煽动小股东情绪,号召罢工、罢市、罢课,借群众事件向政府施压。于是,有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。
在雪珥笔下,这是一场既得利益集团挑拨官民关系的案例。利字当头,运动往往与正义、非正义无关。
记者:所谓的在显微镜下看中国近代史,你是怎么去做的?有关保路运动的历史细节,是如何获得的?
雪珥:因为在国外生活的缘故,我能接触到不少西方的历史记录,研究资料来源不局限于国内,也不局限于当事的某一方,片面的材料只会导致不客观的结论。在历史研究中,我会使用律师思辨的方法,把各方提供的细节摆出来,由此推出结论,不言自明。
台湾出版的200万字的《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》我精读了两遍,真实往往藏在被忽略的细节中。就算“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”,通过细节上的仔细比对,也能看出这个小姑娘当年的眉毛、眼睛大体是什么轮廓。
因为当过记者,写东西会考虑怎样的叙事更吸引读者。但事实上,我的文章细节句句有出处,连天气、景色的描述都有资料来源。
记者:对于历史的解读,大众的接受能力已经不再局限于教科书结论,也不再满足于主流提供的观点。你挑战了哪些主流的观点?
雪珥:在历史研究上,我不是很同意统治阶级、被统治阶级阵营这种二元论的划分,而是倾向于三元论——把人群分成官、民和既得利益集团三个阵营。官和既得利益集团有一部分重合,但不完全等同。官想要天下太平、国富民安,这和民的利益是一致的,既得利益集团却有可能成为改革路上的绊脚石,保路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
记者:历史上“正”和“邪”的分野,随时可能发生颠倒。对恭亲王、慈禧、康梁等历史人物,你都表现出自己的判断。你的历史观是怎样的?
雪珥:官方主导修史,多半只是为了一个短期的目的。有话语权的一方,总是把自己打扮成“天使”,把对立的一方打扮成“魔鬼”。事实上,既没有“天使”也没有“魔鬼”,历史事件中的人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凡人。
我的历史观可以用三点来概括,说来也是“一个中心、两个基本点”。
“一个中心”,就是以“人性”为中心。我认为,在研究历史的时候,应该从人性切入,而不是从任何意识形态切入。很多历史事件中,其中人物的种种行为,究其原因不是因为他信奉什么主义,也不是因为他属于什么党派,而是因为他个人所处的位置、利害关系。其中起最根本作用的,是“人性”。“两个基本点”就是“利益”和“权衡”。利益是每一个人的处境,也就是你的“位置”所决定的你的利益需求。不同的位置,利益是不同。比如,做一名记者的利益是多写稿,写好稿,多拿稿费。但是同样一个人到了宣传部,他关心的重点就是新闻媒体别给我惹事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屁股决定脑袋”。
与此同时,不同的人在同一个位子,会表现出不同的原则和底线,作出不同的选择。当事人会去“权衡”,有的人会说这种事我万万不做,但有的人就无所谓。这是“立场决定观点”。
第二次鸦片战争后,清政府建“总理衙门”,不仅处理外交,而且承担了对内改革、对外开放的相关职责内容。这像是一个今天的跨部门委员会,总理衙门大臣不是专职的,而是由各部大臣中挑选了兼任。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,恭亲王就很巧妙地让反对者兼任总理衙门大臣,给他们压担子,成功地将所谓的顽固派、保守派,转换为改革的同行者。毛昶熙和沈桂芬就是这样被他感染而同化的。
记者:所以归根结底,你赞同“实用主义”是历史人物抉择的出发点,这也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?
雪珥:没错。我在政界工作了10年,在商海游泳了10年,以我的所见所闻,似乎并没有人脱离这“一个中心、两个基本点”。我不怀疑有人是“纯理想主义”,但这种人太稀有了,很难看到。
超速致倾覆
改革开放始于晚清
1923年,上海《申报》回顾了前60年政府对经济的扶持。社论认为,晚清九年是最好的时间,民国十年最黑暗,对比两任政府对实业发展的扶持力度,有“贤、不肖之别”。
雪珥认为,晚清王朝的政经改革史无前例,且卓有成效。最终王朝覆灭的原因不是改革不行,而是改革速度过快,导致了帝国的脱轨。
记者:80多年前媒体的这一评论,会不会是刻意厚古薄今、针砭时弊的舆论监督?
雪珥:不会。当时私营企业的发展情况、政府在财政上的支持,都有史实可以证明。
中国的改革史,始于1860年代恭亲王所推动的改革,至今已经超过了一个半世纪。从1860到1911年,晚清的50余年其实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根基和民族心理根基。
晚清的政治改革其深度、广度、力度,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。与我们一般以为的情况不同,晚清最后6年,尤其是1909-1911的宣统朝的3年,国家并非每况愈下,政治、经济乃至国防都在不断进步。比如,1908年时,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首次突破了白银2亿两大关,史无前例。而政治上,到1909年除新疆之外,全国各省都建立了地方议会,对地方行政领导实行非常有效的监督,这也是史无前例的。中央层面上,作为国家议会的资政院也随后成立。
记者:你认为以恭亲王为源头的晚清改革,是行之有效的改革?
雪珥:是的。我们经常批评1911年推出来的责任内阁,说它是“皇族内阁”。但是,这个“皇族内阁”并非传统概念上的权力极大的内阁,而是新型的、在国家议会的监督下的责任内阁,是个弱势的政府。这一点一直被忽略。这届内阁的总理、庆亲王奕劻也干得很别扭,多次想撂挑子。
记者:既然晚清的政经改革得力,为什么还会灭亡?
雪珥:1911年时,很少人认为这个政权会突然崩溃。但是,武昌城头一声枪响,这么大的一个政权土崩瓦解。主流的解释说是清政府假改革、改革太慢,而我认为,恰恰是因为清末的新政改革太快,导致超速失控。
立宪运动启动后,从三权分立转为地方自治,实际上导致了立宪运动的变异,成了地方分离运动。一个很典型而被广泛忽视的情况是,到1908年,中国的年财政收入超过了2亿两白银,这是史无前例的,但中央财政所能掌控的,只有区区2400万两。一个政权,丧失了对88%的财政收入的掌控能力,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作恶的能力,更失去了制止作恶的能力。在某种程度上,它已经成为一个傀儡。
美国的政治学家亨廷顿,深刻地论证过改革和革命的关系,他认为改革的推行必须依靠权威资源的保障,没有这一保障,改革一定会被人利用,最终走样,而成为改朝换代、取而代之的工具。到了1911年,武昌城头一声枪响,几个造反的军人,就引爆了一个政权的垮台,并不是什么革命的力量,而是这个政权早已四分五裂了。
民主的实现
关键是政治土壤改变
采访中,雪珥不止一次提到对韩寒的欣赏。他愿意看到更多年轻人对革命持一种理性的态度,这也和他的观点不谋而合。
“对于一个开车时连打远光灯近光灯的规则都无法遵守的民族而言,激进的革命只会带来大规模的无序和灾难。”雪珥说。
记者:晚清改革的轨迹被辛亥革命打断,你认为这延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,是这样吗?
雪珥:从甲午战败后,中国进入了一个寻找“制度灵丹妙药”的阶段。精英阶层,尤其是体制外的精英,将社会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制度乃至执政者,以为换个制度——往往是换个制度的名称,换个执政者,就一切迎刃而解。这在之后的历史中,成了一种潮流。
精英们乃至全社会,不断地在“改制”的折腾中颠来倒去。辛亥之后,中国社会陷入你争我夺的夺权混战之中,鲁迅说是“城头变换大王旗”。各路人马打着动听的口号,其实只是为了夺权。甲午战败后带来的这股“主义”万能风潮,对中国的现代化造成极大的困扰。
政改不是换一拨人来当权。主义、意识形态都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。
记者:你相信改革的效率要比革命更高?激进的革命对中国而言并不适宜?
雪珥:是啊,毫无疑问。治理国家就像运营一个公司,不停地更换股东,并不能带来公司效益、员工福利的提高。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更好地经营公司。
这其实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。公司治理是一门科学,国家治理更是一门科学。想要改善国家机器的运行状况,为什么不从实现司法独立、舆论监督、决策公开透明这些具体的层面去操作,非要拉下一群狼,换一群更饿的狼上台呢?
记者:建立更民主、更先进的政体,难道要靠执政者的自律来实现吗?
雪珥:没有任何理论敢于相信“自律”的力量,要靠更科学的管理制度来实现,即便是表面上的自律,也要靠外部的制衡和惩罚机制保障。必须注意的现实情况是,任何一个执政集团内部,都不可能真的万众一心,而存在内部的利益博弈,也有望形成内部的权力制衡——这也是执政集团自身健康的保障。晚清50年,“垂帘听政”和“亲王辅政”这种“叔嫂共和一国两制”并存的模式,令体制内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权力分立和制衡。
权力本身是恶的,折腾只能带来更多无谓的消耗。我认为,关键是如何在技术层面寻找更科学的治国方法,去制约权力。民主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,最根本的是政治土壤的改变。
 |
大众网版权与免责声明
1、大众网所有内容的版权均属于作者或页面内声明的版权人。未经大众网的书面许可,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大众网的各项资源转载、复制、编辑或发布使用于其他任何场合;不得把其中任何形式的资讯散发给其他方,不可把这些信息在其他的服务器或文档中作镜像复制或保存;不得修改或再使用大众网的任何资源。若有意转载本站信息资料,必需取得大众网书面授权。
2、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,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,并注明“来源:大众网”。违反上述声明者,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。
3、凡本网注明“来源:XXX(非大众网)”的作品,均转载自其它媒体,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,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。本网转载其他媒体之稿件,意在为公众提供免费服务。如稿件版权单位或个人不想在本网发布,可与本网联系,本网视情况可立即将其撤除。
4、如因作品内容、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,请30日内进行。